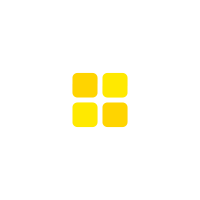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2017-10-21 12:55
如今,我们生活在既感性膨胀又理性宰制的时代。说感性膨胀,是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已使我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的感性愉悦体验,生活的品质就是品味和体验的快感。说理性宰制,是说今天科层化现象日趋严重,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深度入侵,学术研究越来越理性至上。
其实,人本身就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俗话说得好,合情合理,此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但感性和理性并不总是和谐相处,席勒最早指出了人性的现代分裂,他主张用审美来弥合感性与理性两种冲动之间的裂痕。二十世纪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进一步彰显了这一主题,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人格结构的考察,指出人格结构的内在冲突是本我和超我的对立,因此需要一个自我来加以协调。社会学家韦伯则从另一个角度发现,现代性是一个不断科层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价值领域的分化导致了审美的独立,因此,艺术成为对抗理性化的某种救赎:
生活的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情境,因为在这些状况下,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这些价值本身就存在。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①
如果我们把社会学的观察和心理学的发现结合起来,就会注意到,现代社会的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乃是我们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关于这一困境的说法很多,诸如感性与理性,爱洛斯与逻各斯,情和理,结构与解构,甚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这个困境不仅体现在社会文化的宏观层面,也体现在艺术界关于艺术边界的争议中。本文从艺术家之感性和美学家之理性的分立对抗出发,来探究为什么艺术边界的问题挥之不去,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困扰着艺术界。我相信,艺术边界的问题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界定或思辨的问题,毋宁说,它是由艺术界内部不同角色—艺术家和美学家—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现代性问题。
稍有艺术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艺术边界问题在传统文化中几乎不存在,只是到了现代才成其为问题。现代性的进程凸显出艺术的两面性,一方面,现代艺术的激进和反叛不断地改写着艺术的版图;另一方面,美学理论雄心勃勃地界划出艺术的边界所在。这一颠覆与规范、变动与固定、越界与划界的两极运动,就好像始终有两种对立的力量牵制着艺术界。于是,艺术的边界总是不停地困惑着人们,并引发了许多争议和激辩,提出了林林总总的解决方案。如果上述描述是真实的,那么,问题就转换为这两种彼此对抗的力量究竟来自何处?
我以为,用文化社会学关于艺术界构成的理论来看,两种不同的力量就源自艺术界里两种最重要的行动者:艺术家和美学家。假如说艺术是一个有着特定版图的王国的话,那么我倾向于将艺术家设想为艺术这个王国里充满激情的拓荒者,而把美学家比作这个国度理智的测量员。艺术的发展一再向我们揭示了一幅真实的图景:艺术家总是一往无前地开拓疆土,发现新大陆;而美学家则忙着丈量艺术家所新开垦的处女地,描绘出王国疆土的地形、地貌和边界。把这一关系加以简化,对艺术家而言也许根本没有什么疆界,他们想跑多远就跑多远,而且总是以一种充满激情的感性冲动来颠覆界标;美学家则不然,他们要理性地思考各类艺术的根据和缘由,拿着各式各样的尺子来丈量艺术的新大陆,告诉人们艺术王国的国土已
经拓展到何处,这些拓展是否合适,新开垦的土地价值如何。艺术家和美学家的这一感性开拓者与理性测量者关系,其实就是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的关系,此乃艺术边界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根源。
如何证明这一经验的观察呢?
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中,艺术并无独立自主的地位,它屈从于传统、宗教、伦理和政治等,因此艺术边界的问题尚不存在。当艺术随着现代性的进程而成为一个如韦伯所言的独立的人类文化领域时,其边界问题才凸显出来。更重要的是,现代艺术,特别是现代主义艺术,充满了变革和反叛,最富创造性的艺术家往往就是最具颠覆性的艺术革新者。现代主义各种流派风起云涌,彻底打乱了艺术的地形图,于是,艺术有无边界或在哪里就成为一个难题。比如,讨论现代艺术边界问题时被经常提到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个是司空见惯的男厕所里的陶瓷小便斗,被法国艺术家杜尚命名为《喷泉》,它就莫名其妙地从一个日常生活的器具转而便成为一件艺术品;第二个典型例子是美国艺术家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一个在超市和家居中常见的包装盒,被排放在美术馆里展出而成为一件“艺术品”。这两件物品本身并无什么特别的价值,和日常生活中的同类物品别无二致。但它们被授权后就摇身一变,成为挑战现有的艺术边界的利器,因此而具有某种令人振聋发聩的棒喝功能。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什么可以成为艺术品?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界限何在?谁有权命名艺术品?何种体制可以接纳并标签其为艺术品?有趣的是,这两件物品(或“艺术品”)如今已被美学和艺术史所认可,并当作艺术边界问题的一个极端而又典型的例证,在美学、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中被反复引用。长期思考《布里洛盒子》的美学家丹托,为此发明了一种美学理论—艺术体制论—来解释这一形象。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说:“将某物视为艺术品需要某种眼睛所无法看见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一言以蔽之:艺术界。”②
从比较的角度看,艺术家是艺术王国的激情开拓者。他们一是开拓者,他们不断地扩大艺术的版图,颠覆艺术史业已形成的种种规范和价值评判标准;二来总是充满激情地创新,感性创造甚至颠覆,既是艺术创作活动的特点,也是艺术家的职业特征。那么,面对艺术家的这种开拓,美学家们在干些什么呢?他们的任务、职能或角色是什么?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艺术史并不只是由艺术家及其艺术品所构成的历史,同时也是艺术研究和艺术价值争论的历史。没有美学家或艺术史家的参与,艺术史是无从谈起的。前引丹托的名言即如是,所谓“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说的就是一种由美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共同参与的活动所协商形成的场域,即所谓“艺术界”(The Artworld)。当然,这里我关心的并不是艺术体制及其解释,而是在这一体制中艺术家和美学家所扮演的两种不同角色和功能。如果说艺术家是艺术王国的激情开拓者,那么美学家就是这个王国的理智测量者。一如艺术家的激情与拓荒,美学家亦有其两个鲜明特征,那就是理智与测量。所谓理智,说的是美学家的理论思维的特点,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理性的、逻辑的推理和论证,来确立艺术的边界;所谓测量,也就是对不断改变着的艺术王国的疆界进行丈量和勘察,得出边界何在的理论判断和结论。
这么来看,艺术家激情拓展,美学家理智划界,现代艺术界的智力分工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所以艺术边界就必然呈现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俟美学家把艺术家业已拓展的边界测量界划出来,竖碑立界,不安分的艺术家又越出了界限而拓展新的疆土。一边是划界竖碑,另一边是越界拓展,这一张力关系导致了美学家的艺术边界持续不断被艺术家所打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艺术家和美学家的两种角色及其功能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无法克服的对立,因此,艺术边界永远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柏拉图在谈到美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美是难的!”模仿柏拉图的话,我们可以说:“艺术边界问题也是难的!”
其实,艺术家和美学家的张力关系,从某个角度印证了人类文化的感性和理性二元结构。别说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在每一个人身上存在,就人类文化的宏观层面来看,两者的冲突对抗亦无法消除。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两半球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即左右半球各司不同的功能。一般说来,右半球掌管着空间认知和情感体验,而左半球则掌管着语言和逻辑。宽泛地说,右半球是感性半球,而左半球是理性半球,虽有脑干相连接,但感性和理性的差异和区分是很难消弥的。个体尚如此,文化更如此。宽泛地说,艺术家是更有赖于右半球功能,而美学家则更偏重于左半球功能,不同的偏重形象地揭示了艺术感性实践和美学理性研究之间的内在张力。心理学的另一个发现是思维类型的区分,如果把人类复杂的思维区分为一个两极对立结构的话,那么,最典型的两种思维方式是所谓发散型思维和聚焦型思维。前者的突出特征是不拘一格的开放性或离心式思考,颇有些古人所谓“精骛八极”的意味;后者则更倾向于规范的、理智的向心式思索,更强调思维的规则和推理。根据心理学家哈德逊的研究,有艺术气质的人或艺术家是前者突出的代表,而物理学家则是后者的典型。③如果把这两种思维类型用于描述艺术家和美学家,显然艺术家是长于发散型思维的人,而美学家则是倾向于聚焦型思维的人。艺术家不但以发散思维来创新,也以发散的方式来拓展艺术的疆界;而美学家正相反,他们总是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来反思艺术家的发散之举,用更加聚焦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或规定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杜尚和沃霍尔的“反艺术”颠覆就是一种典型的发散思维和行为,而丹托对这一现象的体制论阐释则是对发散思维的聚焦式解说,给出确切的答案来解答艺术家所提出的艺术难题。
回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关系角度来陈述,即本我和自我的关系揭示了艺术家和美学家在艺术边界问题上的角力抵牾。弗洛伊德认为,本我乃是人最具本能性的冲动,是发自艺术家心理深层的原初冲动,如同白日梦。在他看来,本我的冲动是无拘无束的,因此,需要有另一种力量来制衡,这就是所谓的自我。本我是原初冲动,依照快乐原则行事,而自我是继发冲动,依现实原则行事。艺术家本我冲动的快乐原需要通过其自我的现实原则来加以调节。形象地说,本我像一匹野马,而自我则是一个驾驭野马的骑手。假如把这一原理推广到艺术家和美学家的关系,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艺术家对艺术的越界和颠覆,就是依照本我的快乐原则来行事的;而美学家的工作则是依照现实原则来对艺术家的本我冲动加以规范。如同弗洛伊德所作的比喻,一如野马和骑手的关系。艺术家要挣脱美学家的驾驭,而美学家则努力界说艺术家无拘无束的冲动。所以,艺术边界就总是呈现为一个难题。
这一关系可以从更加广泛的文化社会学角度来解析。回到开篇曾提到的韦伯著名的现代性理论。他认为,现代艺术的确立是一个逐渐和宗教伦理相分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宗教伦理对艺术表现内容的制约慢慢地消失了,艺术表现什么不再受制于宗教伦理信条。于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或表现性被当作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凸现出来。简单地说,艺术的评判标准不再是宗教伦理,而是依据艺术自身的审美价值。由此导致了强调审美价值的现代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领域而出现,这是现代艺术产生的重要根据,韦伯概括为诸多价值领域的现代性分化。他进一步指出,现代艺术一方面会是理性化的现代性分化之产物,即艺术(世俗)与宗教的分离;另一方面,艺术在获得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之后,反过来又对日益理性化的社会具有某种纠偏作用,亦即为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提供某种不可或缺的感性愉悦。遗憾的是,韦伯虽指出了宗教和艺术的分离是现代艺术得以出现的原因,但他却没有仔细考量是谁对此产生了助推作用。如果我们把韦伯的理论和另一社会学家鲍曼的研究结合起来,答案便会昭然若揭。鲍曼发现,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崛起,实际上是和美学家所扮演的“立法者”角色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期间发生了一场持久的“发现文化”的运动。韦伯所说的艺术脱离了宗教而日益强调审美特性,其实正是经过美学家的长期艰苦的“立法”工作才得以完成。美学家们通过对艺术的理智论辩而形成了现代美学理论,进而确证了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类文化领域的合法性,它特别呈现为艺术所特有的审美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呈现为艺术的良好审美趣味,进而呈现为现代艺术的边界和特征。他写道:
在整个摩登时期(包括现代主义时期),美学家们依然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在美学领域,知识分子权力看来尤其未曾遭到质疑,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垄断了控制这个领域的权力。……教养良好、经验丰富、气质高贵、趣味优雅的精英人物,拥有提供有约束力的审美判断、区分价值与非价值或非艺术判断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往往在当他们的评判或实践的权威遭到挑战从而引发论战的时候体现出来。④
浪漫主义时期,雪莱曾褒奖诗人是未经公认的“立法者”。其实,更重要的“立法者”恐怕不是诗人或艺术家,而是美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有研究发现,在现代性条件下,美学家(或批评家)和艺术家的不同工作是现代文化的某种劳动分工:由于美学家往往比艺术家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了其作品,所以艺术家的某些权威也就部分地转移到了美学家身上。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艺术家与其说是独立自足和自决的主体,不如说是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和批评赋予他们以权威和力量。于是,可以说艺术家最终不过是美学家美学理论和批评的产物,而非自己作品所造就。⑤这种说法看似有点夸张,但却真实地道出了美学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在确立艺术边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极为重要的角色。美学家是“立法者”,也就是说他们在艺术王国的发展中的勘测和描绘版图的功能,具有宣判艺术家及其所发现新大陆是否合法的作用。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一个结论性的看法。艺术的边界在现代始终是一个难题,它挥之不去又反复出现。它之所以不断出现,原因之一就在于一方面美学家们总是不停地划定艺术的边界,另一方面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又在不断地突破美学家划定的边界。这就构成了一种张力性的无限循环!更进一步,对于艺术家来说,所谓的艺术边界也许并不存在,恣意妄为地天马行空是他们的本性;对于美学家来说,没有边界的艺术将不再是艺术,没有边界遂将取消美学家存在的理由,只要有美学家,就免不了要去界划艺术的边界。艺术家感性突围和越界,美学家理智测量与划界,这一张力关系构成了现代时期艺术边界亦破亦立的关系。所以说,艺术的边界就在艺术家之破与美学家之立的动态过程中。
注释:
① H. H. Gerth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342.
② Arthur Danto, “The Artworld” , Carolyn Korsmeyer, ed., Aesthetics:The Big Questions , Oxford: Blackwell,
1999, p.40.
③ Liam Hudson, Contrary Imaginations , London: Methuen, 1966.
④ [ 英] 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179 页。
⑤ Donald E.Pease , “Aut hor ”, in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eds., 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ies , Chicago:University Press of Chicago, 1995, pp.110-12.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周宪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