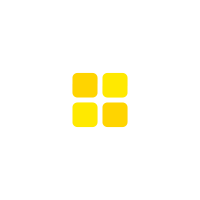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2018-01-19 15:13
在近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生涯中,艺术家田世信以桀骜的个性和骨子里的坚韧持续着他的人物雕塑。不论是近40年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还是风云变幻的艺术潮流,都始终没有动摇他在雕塑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中建立起来的尊严,更没有改变他对世人命运,特别是乡土人间的悲悯和关注。难以想象在他经久多年,如此巨大而丰富的创作中,竟然没有一件非人物,非具象的创作。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人物或者头像展开,这让他的艺术成为中国雕塑界一个具有开创而又独特的个案。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田世信的在这40多年的创作轨迹中,他既没有滑入到一种单纯的抽象语言或者材料的实践,也没有转向一种观念性的创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创作就缺乏观念,或者缺少材料以及语言创新。相反,田世信最不缺乏的就是对于材料的实验,几乎所有能够用于创作雕塑的材料都被他尝试过。特别是近年来,他更是与民间工匠合作,全身心投入到大漆材料的反复琢磨之中。而在雕塑语言上,我们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他都能建立起独特而自足的语言体系,从最早夸张、稚拙、民间,这种自由而充满激情的刀劈斧砍式的创作语言到后来探究、复古、执拗,崇尚传统审美奇人异相的造型语言。
对处于不同生存环境和历史背景中的人物,他能巧妙而不失贴切的把握到表达他们个性、精神和音容面貌的语言形式。然而对于田世信来说,不论是对材料的不断尝试,还是对雕刻语言的反复推敲,其最终的目地却是为他最朴素的观念——人文关怀——来服务。因此上,他的创作路径始终没有陷入到对纯粹艺术的追求之中,这也决定了他的作品在表面上与形形色色的当下创作显得格格不入。这应该是老派——在历尽劫难的社会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一致选取真实、鲜活、自由的人物范式来持续的回应和批判伪饰的虚假社会现实主义成为他们持久的共性。所以,反观田世信的整个创作历程,无不发现他的创作与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之间紧张而寓有深意的关联,这是老派艺术家坚守的可贵品质。
每一个艺术家注定无法逃离特定时代的局限,但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能对时代的症结做出独特的反应。作为新潮时期崛起的艺术家,田世信和那个时期的艺术家一样,也深深的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他崭露头角,第一次亮相就惊艳观众的作品是贵州边陲的少数民族系列。批评家孙振华说“他早期的作品《侗女》、《苗女》、《欢乐柱》为中国当代雕塑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方向,即表现在贫困和艰难中挣扎的少数民族,表现他们寄寓于平凡而又普通的坚韧顽强的精神世界,以及在艰辛中透露出来的崇高感。”①这些被笼统的称为乡土艺术的雕塑有着时代的共性,中国现代艺术的变革从蛮荒边缘的原始之地找到了一个松动的缺口,为中国雕塑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
应该看到,在同一时期震惊一代人的绘画作品中,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等都是边远、朴实的少数民族人物。转型时期的艺术家不无意识的抓住少数民族题材,这是艺术长期被功能化后的本能反弹,选择少数民族题材,首先是艺术家开始争取自由的结果,这个当时整个时代所弥漫出来的鼓动人心的气息,敏锐的艺术家迅速的抓住了时代涌动的脉搏。回到具体的艺术创作中,选择少数民族还包含着艺术另外一个重要的品质——真实。无疑少数民族朴实、粗旷、憨厚,乃至原始的生活感动了艺术家,反过来也正是这种原汁原味的劳苦人民成为艺术家反对以往样式化、僵硬化的伪饰现实主义最为直接和有力的内容。当然,这里面还暗含着艺术家的一种情感,即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勇气和精神命运的惊叹与思考。
正是各种合力的交织和解冻时期的一股春风中,艺术家在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将艺术重新回复到独立、自由、真实的个性化表达当中。但不同的是,陈丹青用欧洲油画的方式取代苏联画法还是罗中立超写实,所运用的绘画方式依然是学院化的,且就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少数民族之间,或多或少有隔着一层薄纱。但田世信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他在贵州扎根多年(他在贵州生活长达25年,直至调任中央美术学院),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处境对他来说则是日常生活经验本身而不是一个神秘,充满异域风情的陌生情景。所以,田世信的少数民族创作是自然而然,遵从内心真诚,一个更接近民间原始的产物;而并非如其他画家一样是一个艺术史的衍生,一个由上往下观看的学院派产物。因此上,相比于陈丹青潇洒,崇高的西藏人物和罗中立超写实,残酷的大巴山农民,田世信的贵州苗族人物满怀着更多的亲切感和人情味。
当然,身处遥远边陲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因素是他非科班的出身。尽管他早期在北京也受过一些油画和雕塑教育,但那仅仅是艺术最入门的练习。所以当他真正独立面对创作的时候,他全部的不成体系的技艺和自由喜悦的冲动成为他作品最大的特点和支撑。反过来看,非科班出身反而成了他创作的独特优势,少了学院化和其它教条的限制,他完全凭着极大的热情按照自己主观化的理解来创作。然而这并不是说田世信等同于一个民间匠人,没有章法,全靠激情来创作,而是他有张有弛,在实践之中不断拿捏,正是这两点让他的作品与当时的雕塑界显得格外不同。
这就是他最早的《欢乐柱》、《老巴斗》、《侗女》、《节日》等作品,特别是《苗女》这件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作品集中代表了田世信雕塑的艺术特征,夸张的造型,方硬的刀法,凸起的前额,厚实的嘴唇,凝重的神情。透过这些作品具体的视觉呈现,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他对雕塑语言的理解和把握,不拘泥于细节,大胆归纳,高度凝练。这样的语言方式一方面与他表现的少数民族对象之间达成高度匹配,展现出一幅不加修饰、粗旷、淳朴、憨厚,乐天知命的乡土中国。另一方面,如果说高度概括是中国传统雕塑的意象,那么他不仅吸收了传统雕塑和民间雕刻的特色,更为重要的他将中国画中以线造型的方法也运用到了他的雕塑创作中,比如《苗女》的头发走势,《欢乐柱》中的衣服垂纹,《侗女》脖劲纹迹。再到后来的《王阳明》、《李清照》、《汉女》造像的处理中,流畅的线条几乎取代了雕塑本来的体块造型,让厚重的雕塑变的轻盈起来,这和中国文人画中所追求的“飘逸”的审美精神同处一脉。
其实,在“贵州人系列”——特别是那件当时引起巨大风波的《苗女》——之后,田世信有意识的走上了一条重塑古典审美法则的道路。如果说在《苗女》中他以夸张的手法和冲动的激情来刻画少数民族人物的特点,那么在他后来的“与古人对话”系列中,这种夸张不再是一种情绪的支配,而是更倾向于对中国传统审美的经验的重塑。比如《屈原像》、《老子像》、《谭嗣同像》、《司马迁像》、《秋瑾像》等,无不都是额头突出,鼻子崎崛,嘴唇肥厚。从今天的审美来看,这样的面相难免让人不适乃至感到丑陋。但是在古人的文化理念中这不是丑化而是出于“奇人必有异相”的尊崇。传统释道人物绘画,或者石窟、寺庙里的神佛造性,无不面容诡谲,五官奇异。明代著名人物画家陈洪绶的绘画《水浒叶子》最能佐证这种古典文化现象和审美法则。
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形成这样一整套“异化”人物造型法则,归根结底是对于历史上特殊人物的想象,在普通人的想象当中他们肯定异于常人,这样才符合他们所作出的那些超乎常人的举动和所为,所以古典的奇人异相不是丑化而是神话他们。但在田世信的观念中,这种奇人异相却包含着一种求真的态度。对于这些早已被塑造成伟大的历史人物,田世信所做的不再是如何美化他们,将他们塑造成一个完美无瑕的标致美人和圣贤(美人这里特指男人),而是将他们恢复到一个个常态化的人,是一个符合人生百态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的老子耷拉出舌头,司马迁裸露着半身,苏武成为佝偻老人,竹林七贤不是放歌山林,而是裹着破毡蜷缩在地。其中还包括被他反复雕刻的屈原和谭嗣同,两位楚地之人造型特别符合今天湖南人前额突出的长相特征。
奇人异相:古人将历史人物神话为不同与常人的人,田世信却将历史人物异化为不同于平常的他们的他们。通过抓住他们平常之中的偶然状态和神情,来刻画他们的性格,彰显灵魂特质。因此上,田世信重返古典造型法则,并不是仅仅追求一种古典审美样式,而是形成一种对人生的认识。“现在你们认为艺术是表达一种观念和想法,我感觉艺术是表达一种情绪,是一种对人生的认识。”②田世信这样来阐述他的创作。
那么,人生是究竟意味着什么?2004年他创作了一件名为“花桥-人生本是一场热闹戏”的作品。他说“我觉得人这一生,悲伤的时间总是多于快乐的时间⋯⋯这种悲情大戏剧家卓别林演绎、表现过,他所有的喜剧都带有很浓厚的悲剧情结,大笑背后隐喻着大悲。”③这也解释了他的作品人物总是表情凝重,神情悲怆,不论是早期的贵州乡土人物,还是后来的各种历史人物,看不到一个面带喜悦者。更何况他选择的历史人物都是悲惨遭遇者,仿佛神的光芒从未眷顾过他们。从古至今,人世凉薄,让他难以割舍的始终是对这片苍莽乡土的悲悯,这样一种朴素而厚重的信念使得他的作品正好也与那些玩世和嬉戏的大脸绘画形成鲜明对照。
田世信说他不排斥创新,但他更愿意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不是说他固步自封,而是他也坚信变革的价值,只不过他是以退为进,总是从传统之中寻求变革的因子。这就是当其他艺术家从雕塑转向装置的时候他依然坚持雕塑,当其他艺术家运用西方语言创作的时候他却找到传统造型手法,当其他艺术家试验新的材料时他却倾注极大热情进行大漆这种传统材料的试验,他的《王者之尊》应该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以及如何将绘画与雕塑再次结合起来尝试。在他看来,传统中还有很多很好且值得挖掘的东西,一味的抛弃并不见的就是创新,而可能是一种盲目和不自信的表现。
作为曾今影响了一代雕塑创作的人物,田世信并没有止步于过去的成功模式。对于艺术创作这种充满未知和不确定性的工作,他有着特别朴实和清醒的认识:“雕塑在创作制作的过程中,有一种引逗的力量,这是我总是精力充沛地完成他。我非常喜爱这个事业,以往常乘火车路经中原,去时一片汪洋,归时耕地干裂的像中国碎瓷的图纹。但是那里的农民没有去理睬这样‘法定的’灾荒。每年照常执着的将种子播下去,我欣赏他们的执着。”农民不会因无法预知的结果而放弃播种,真正的艺术家也应如此。在半个世纪的辗转腾挪之后,他依然我行我素,刀耕不辍,这是他对艺术的执着,也是对这片苍天厚土的深沉眷恋。
注释:
①孙振华:《转型的年代——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当代》杂志,2012年第2期,第40页。
②李梦虞、谭莉:《雕塑三人谈:田世信、隋建国、展望》,《折腾一得:田世信艺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18页。
③李梦虞、谭莉:《心念50年》,《折腾一得:田世信艺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31-32页。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康学儒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