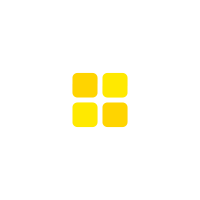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方向嘱我写点东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呈现出一些影像来:沃红的楼阁,摇曳着水乡庭院,波光荡漾,带点静谧的回荡,传统的田园显现出一种新的视觉时尚与性感。或许,出现这样的感觉有些不合适。但不知道是他嘱托时的认真态度,令我感到一种写作的压力,还是他的画面天然带点挑逗的情绪,让我无法回避如此的联想。其实,画面本身就是一种单纯视觉上的经验呈现,只要它能撩起观者某种沉睡的感受,由感观触发情绪,忘却一些生活的琐碎,得到些许超脱,即使这种情绪是不可言说的,它也有着自己视觉上的价值。所以产生怎样具体的情绪,似乎并不重要。如此这般说,并不意味着我的感受就是方向想向我们传达的东西。应该说,每一个画家都是丰富而复杂的视觉现象,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明了,有时甚至就是语言所难能表达的。绘画本是感性,画的时候、看的时候都只是一种情绪影响着我们的感受与判断。当我们试图描述它的时候,也许我们即已背叛了它。但我们仍需极力地用语言去捕捉这瞬间的视觉感受,抑或经验。因为,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与画神交的欣赏,能够获得别样的审美快感。但,它绝对只是私人空间的经验描述,可以没有任何理由,也无需任何原因。只要,我们能在这份描述中感到一种莫名的读画情绪,就足已。
我不晓得方向是否知道我读画时的这份感性的散漫,但我明白,方向看重的是我与他聊天时的理性与判断。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们闲坐于他广州市区的画室。屋里的摆设是旧式的家具,砌上一壶乌龙,我们随便就着寒暄便聊开了。我是一个容易投入话题的人,容易激动,一旦谈话的内容触动了我所敏感的东西,思绪与口腔便同步高速。方向为人安静,我们动静相配,倒是投机。当提及他的画时,我相当主观地说他走了一条时尚新颖与传统笔意之间的中间路线,未想他竟然默许了,并嘱我将这种想法写出来。于是,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了我开篇所描写的那种场景感觉,很是直观地转换了我对他的画面的记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换,我不清楚。但潜意识里还是感觉有些不合适,尤其是跳出性感之类的词汇来,似乎与方向兄的画面有点远。于是我便努力消除这样的想法,然而越当我试图消解这样的联想,它就越发顽固,顽固的犹如藤蔓纠缠于思绪之中,很难厘清。于是我明白了自己大脑是如此的散漫,散漫得你愈想控制,它就愈发努力地摆脱你的控制,丝毫不理会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偏见。佛语所谓“我执”,可能就是如此而来的。
是啊,我们的大脑时常会犯上这样的毛病,习惯一种东西之后就成为标准,很难摆脱。画家也是人,当其接受某种传统的视觉典范时,传统便成为一种习惯,中国画根深蒂固的笔墨程式尤为如此,它仿佛天然就具有某种对抗新生视觉经验的免疫力,从而确保了自我语言体系的纯粹。试图打破这种体系以期获得新的审美体验,是二十世纪中国画不可回避的命题。然而,打破并不是破坏,中国画独具价值的经验恰恰正是它多少年来形成的有关笔墨语言的整套审美心理。如果一味求新而完全破坏此种审美习惯,则无疑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消解了中国画之本体。二十世纪以写实为目标的中国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忽视了这一点,从而难以确立它于二十世纪中国画演进中的建设价值。方向生活在岭南,是为岭南画派的核心区域。或许历史的步伐早已消解了上个世纪岭南革命派与保守派的纷争,但岭南画派因其革命而消解中国画传统意趣的历史姻缘,则似乎没有随同历史的远去而消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初识方向时,便稍感诧异:他是岭南地区为数不多的能让人感受到较高传统笔墨修养的画家之一,并且还如此年轻。
所以,一次与朋友聊天论及岭南画家,有人说方向是岭南画派最新的代表时,我表现出了否认的态度。首先岭南画派是一个历史名称,它是否延续到今日还是一个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我们自然不能轻易定论谁谁的归属问题;其次,就绘画本体而言,方向对传统笔墨语言的深入和消化,与岭南画派注重光影忽略传统笔墨意趣有着较大差异。就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作品而言,方向九十年代初期的作品中就显现了这种差异。那一时期的作品如《秋凉月淡行客少》、《农家乐》、《深院》等,笔线皴擦之间的语言关系已经成为了画面自觉追求的表达方式。虽然他没有选择传统山林野逸的题材,而将刻画目标确定为生活化的场景院落,但就语言本体的呈现而言,他与传统文人山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而这一点,或许正是方向身处岭南却能游离其外,获得自身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方向外表从容、平静,与人谈话时总是那般笑容可掬,仿佛永远没有脾气一般,但他的眼神总是流露出另一种细腻与敏感。我想,方向的内心和他表现出来的平和是有点出入的。最起码,他对细节的感受能力比普通人要多一些。因为从一开始,方向的画面中就呈现出多种视觉经验混合的效果,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正是对各种画面形式有着较为敏感的感受与转化能力,其中,对于传统笔墨经验的感受与转化能力自然更为重要。
就方向的早期作品而言,他以笔墨语言为中心,吸呐二十世纪“美术变革”在场景叙述与表达上的成绩,乃至一些民间艺术的色彩感觉,初步形成了他的画面独特性。或许,观者可以找到一些笔线细节上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言,他在坚持传统山水语言之审美经验的基础之上,改变传统山水以“境”为中心的表达,倾向于以“景”为中心的描述,并呈现为带有他独特视角的田园景观,确是当代山水画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尝试之一。并且,他的某些作品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一些林风眠的影子。如《疏林老墙落照中》、《一路山歌》、《轻云闲步》等,在带着一点色相的墨晕中,突出了线条的造型能力与表达空间。虽然他的线与林有所差异,然而林将墨晕融为色彩的氛围,无疑对方向有着一种潜在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确定方向画面呈现出的这种影响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还是一种无意识的显现。但我们却能从画面中切实地感受到他对这种视觉经验及表现方式的敏感度。其实,在方向的画面中出现林的影响,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因为林风眠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变革的方向上,与岭南画派以光影改造中国画的选择差异甚大。他更倾向于保留中国画的传统趣味,试图将西画的构成感融入传统水墨的审美表达中。而方向生活在岭南画派影响深远的广东,但从一开始的创作中,却更加注重与岭南画派差异明显的林风眠,似乎显现出他在求新求变的探索阶段对于传统的另一种形式上的偏爱。这种偏爱,或许出于天性。因为对视觉经验的选择与吸收,需要一种发乎本性的敏感,一种天然的对于形式氛围与笔墨经验的感受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僵化的模仿,而难以将这种感觉消融在其它的视觉语言中,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呈现。
方向对传统的偏爱,在岭南地区有着他一定的独特性。对此,他有着自己学理上的认识,而非简单的感性把握。正如他曾经在《中国画家的尴尬与期望》一文中写道:“二十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画一直扮演着被改革的对象,不少人认为中国画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必须用素描来塑造,来表现我们身边的新事物,‘科学’地‘实用’地改造中国画。经过风风雨雨几十年,中国画从某些方面来看确也进步了不少。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画家对自身素质和笔墨能力培养的轻视,导致中国画的精神和其独特的笔墨情趣不断地减弱。”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方向表现出了和他周边画家不太相同的对于传统笔墨的重视和追求。但就画面最终的呈现而言,方向并不是“传统”刻板的信徒。他的画面在选择上显现出一种机智的灵活,很善于将不同的视觉经验混合出新的感觉来。他似乎没有像浙江的很多画家一样,深入到传统临摹中寻找笔墨的精微,而更在意直观上传统笔墨的氛围,并巧妙地将这种氛围转化为他的视觉营养。在这一点上,他用他的灵活性消解了笔墨传统对于新视觉语言的免疫力,从而将传统的笔墨程式简化为一种呈现过程中的元素,为他自己的画面争取到了更大的表现空间。我不清楚方向本人是否意识到他对待传统笔墨的这份机智与灵活,因为理性思考层面上的看法与实际操作层面上的表现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画家自己的体会才能清晰地感受到,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对于物质语言的操纵感。
应该说,方向对物质语言的操纵感,或者说绘画的手感,是有着相当天赋的。他很善于将不同的视觉呈现方式融合转换,成为他自己的表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他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作品——西画空间组合与传统笔墨氛围结合的相对和谐、统一。如果按时间序列排列方向的作品,我们会发现画家的兴奋点是逐渐由庭院之外向庭院之内过渡的。庭院之外的空间相对开放,可以从传统山水空间的表达中获得相对直接的视觉经验,但庭院之内的景观却相对封闭、狭小,需要一个特定的局部视角,从而难以从传统或平远、或高远的空间组合中寻找素材。这种表现方式在传统视觉经验中的匮乏与画家兴奋点的转移,使方向90年代中期作品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新的空间表达与传统笔墨韵致的结合上。此期作品中,《泳池》系列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泳池相对农家庭院,在质地上更加现代。而这种景观上的现代感,对于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往往却成为了一种挑战。因为在很多人手中,要么因为现代感的追求而牺牲笔墨传统,要么则反之。但方向1999年连续创作的几幅大尺幅的《泳池》,却比较恰当地解决了这种现代感与传统笔墨的对立问题。他借助马赛克地砖的描绘,将画面空间切割为向内延伸的地面与地上空间,画面中较难处理的泳池因为马赛克地砖、藤架以及墙体的透视关系而成为地面空间有效的组成部分;而近景大视角的圆桌,与平推深入的桌椅,更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空间次序感,从而形成了与传统山水空间迥异的面貌。并且,方向实现这种新的空间组合的同时,仍然保留了笔墨晕染的技术传统。画面以笔线为骨,在水分的晕化中把握墨与色的变化。于是,一方面笔墨传统因为新的空间表现获得了现代感的质地;另一方面新的空间表现又因为笔墨氛围获得了中国式的静谧与深沉,从而使传统笔墨氛围与新颖的空间表现获得了相对和谐的统一方式。
大约2000年左右,上述探索在方向的画面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面貌。他的庭院山水不同于浙江山水以写生改造明清笔墨样式的路子,或许他缺少一些浙江的精微,但整体上他无疑更现代,呈现出新的视觉表现力。同时,他的图式没有北方山水的厚重与气象,但无疑要多出一些灵动与轻松,显出一种隽秀的抒情感。或许,这正是方向于今日山水画坛独特的价值所在。他很善于烘托场景,通过场景的层层推进讲述他自己关于庭院的理解,以及庭院中的故事。我不晓得是否是岭南庭院的独特性造就了他画面的独特性,还是方向自身对于庭院的理解造就了他画面的独特性。但有一点我却大致可以确定:方向的画面为当代中国画提供了一种未曾出现过的带有精微设计感的庭院景观。他改变了传统山水远观自然的方式,在主观上采取了亲近与在场的姿态,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人清淡。他的庭院充斥着一种生活的情趣——婉转的回廊、散落的案椅、闲适的茶具、丰满的植物、轻松的鸟禽与懒散的家猫,画面流动着一个现代人对于生活的某种热情甚至是关乎“享受”的遐想,虽然这种情绪借助了带有古典样式的建筑加以呈现,但其图式最终呈现的精神状态无疑很现代。
从方向的画面,我可以感受到他对待生活的一种自足的享受感,以及在平淡中寻找生活乐趣的生活状态。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对方向并不了解,对他的描述更多的取决于我对他画面的理解。他的画面告诉我,他与广东的生活非常吻合——轻松的态度中带着一点享乐的惬意,没有沉重的主题,而是沉浸在自我满足的细节感受中。其中,没有理想主义的宏大场面,也没有文人“不食烟火”的山野抒情,方向的画面,带着岭南特有的实际功用主义色彩,在极具微观属性的物质体验中显现出个人化的私密空间。这种对自我现实感观需求的关注,与20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思潮不同,同时也不容于90年代以观念为图式的当代艺术,它在文化品质上相对安逸、相对自足,与“艺术干预社会”的审美理想无关。它不在意图像的象征意味,而在意图像与感受方式的吻合,带有一种市民化的物质享受性。这是一种具有“消费”气质的文化态度,很现实,同时也很实用。或许,这也是方向不具图像意义的图式所能呈现出的一种文化意义,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关注重心发生转移的某种显现。或许,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文化态度,方向于2000年左右初步解决新的视觉空间与传统技术语言的融合之后,就接着开始了一种色彩上的转变。他早期作品的色彩,在调子上偏冷偏灰,多将色彩融合于墨晕之中,降低色彩甚至墨色的饱和度,且多偏黄、绿为主调的混合感。这类色彩在气质上倾向于一种含混的忧郁感,不太轻松。但此后,方向的颜色似乎开朗了起来,色彩更为明确、更为浓重,墨色的晕染感减弱,色的饱和度增强,暖红成为了画面的主旋律,显现出洋气而时尚的现代感,甚至是性感。于是,画面对生活的描述显得更加轻松而欢乐了。他在色彩的书写中,延续了传统笔墨的趣味与氛围,从而更进一步赋予作品一种强烈的现代图式感——传统笔墨的审美习惯被改造为一种全新而时尚的“传统”。应该说,方向生活在现代,他的“时尚”是他不可避免的本性,虽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是一个对传统进行遐想的人。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正是这看似悖论的双重属性,使得方向于今日山水画坛独具一种个案价值,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期待。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理论家)
作者:杭春晓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