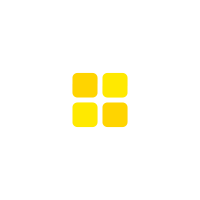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


2018年3月16日,佩斯北京举办萧昱在画廊的第四次个展“易位”
导言:2018年3月16日下午,萧昱个展“易位”在佩斯北京开幕,作为萧昱和佩斯北京合作的第四次个展,本次展览的规模并不大,在画廊左侧空间里,错落分布的8件“易位”新作,用“竹子”的形式感,与观者串联起了一场有关东方美学、材料性、社会现实及危险力量感的多元对话。
2010年北京公社个展“回头”作为萧昱艺术创作的转折。2014年萧昱在佩斯北京实施了首次个展“地”,紧接着是2015年“遗忘,2016年“水泥楼板”,2018年“易位”。这些年萧昱的个展串联起了他个人艺术创作的线索。
展览期间,雅昌艺术网组织了一场【雅昌圆桌】对谈,邀请艺术家萧昱、策展人崔灿灿、策展人李佳作为嘉宾,从2014年萧昱在佩斯北京实施的第一个个展“地”到最新的个展“易位”,解读萧昱多年来的对艺术的内在思考。

2018年3月19日,【雅昌圆桌】萧昱的艺术创作在佩斯北京举行,左起为嘉宾:策展人崔灿灿、艺术家萧昱、策展人李佳
本文整理自:2018年3月19日 【雅昌圆桌】从“回头”到“易位”——萧昱的艺术创作
对谈嘉宾:艺术家萧昱、策展人崔灿灿、策展人李佳
雅昌艺术网:今天在佩斯北京的【雅昌圆桌】,来谈一谈萧昱老师这次展览以及他过去的一些创作。
我们先请策展人李佳来说一说这次看萧昱老师新展览的情况,因为萧昱老师2014年第一次在佩斯北京的展览你就在现场,你怎么看他这几年不同的展览包括新的一些作品?

2014年佩斯北京个展“地”开幕现场
李佳:我跟萧昱老师有比较紧密的这些交流也是从2014年《地》那个展览开始,也是我对佩斯印象比较深的展览之一。虽然已经过去有四年了,但我觉得那个展览不管是对一个画廊,还是对一个展览的体制都有点儿不太一样。我记得那次萧昱老师是把画廊的整个现场变成了一个用水泥做的这种概念的田地,它并不是已经成形的水泥块或是雕塑,而是一个不停地注入和不停发生变化,最后凝固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设计是经过调控的:工人会把水泥浇到已经砌好的一个池子里,同时萧老师从五台山请了一只黄牛,赶着牛去耕这块水泥的田地。田地是水泥做的,在耕作的过程当中不停地发生一些变化,会慢慢地冷却下来,随着人和牛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可能就没办法再走动了。
整个行为被摄像机记录,最后以一件录像作品的形式经过剪辑之后出现在展厅里。观众在表演当天来这个展场看的时候是一个不断凝固的水泥的田地。之后再去看就像我们生活中能够见到那些工地的废墟,或是一些非常平常的土地,看不出来是什么材料,创作的意图也很难去解读,唯一的证据就是墙上还留下一个电视屏幕在不停地回放当时这个牛在耕水泥田的过程。
这里面很多内容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水泥的材料,一般来说我们做展览可能都会把这个材料的性质保留在他最后形成的那个结果里面,但是这个水泥材料的性质其实是挥发在展览的过程当中了。我们今天看到萧昱老师的创作里有很多竹子,以及跟山水或是与古典意象相关的内容。从《地》开始,是有一条线索是可以往回溯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和一个比较稳固的永恒的形态之间的张力。我很想了解一下萧昱老师的创作过程中有哪些故事?

2015年萧昱佩斯北京个展“遗忘”
萧昱:14年的那个展览其实很特别,对我来讲特别冒险,因为在我的表达系统里,非常害怕叙事性。我喜欢控制场域,包括对空间、视觉心理上直接的干预。但做一件有行为性质的作品,甚至把作品录下来这里面就有叙事性,叙事性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如果对语言不熟悉的话很容易就让自己陷入困境。好在我表达本身的欲望是非常清晰的,这样也掩盖了一部分心虚。
那个展览是因为我跟佩斯商量:场地特别适合我的这个项目,因为我需要一块非天然的地,我一直觉得田地其实是人为的,假如没有人的需求,田地就不存在,它就是荒野。它上面长什么本身是由于人的欲望决定的,我把这个田地挪到展厅里边,就是我进一步放大我的看法。
我希望牛把我底下的土再翻出来,我喜欢互相干涉覆盖。工人、农民的劳动太日常了好像都不值得大家说,但是在我的头脑里这两个东西经常混在一起,甚至互相覆盖。所以我希望其中的含义是开放的,不想做过多的对应关系,这样我就有激情去做,而且现场还有一种电影记录的感觉,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去叙述它,我也害怕叙述的那个和我原来的走向跑偏,这样会干扰。所以是诚惶诚恐地在做这个作品,工人在旁边做好以后你马上去把这个水泥在没干的时候破坏掉,表面上破坏,实际上从农耕的角度它是恢复,是重新的建立。水泥给我们的印象都是建构一个新的东西,我在农村生活过,我看农村的很多家庭都喜欢把院子里铺上水泥,南方会好一点,有一些会用青砖,局部露一些草皮。大家的认知是,早期开始有点儿钱的时候都希望再也不要看见土地,院子里全抹上水泥,然后夏天晒的那个水泥会反射烫脸,这个我有着非常深的印象,那是人的欲望在里边一直反复地自我整理。作品表征上是这样,我希望它是开放的,不同的观众进来有不同的认识。好在表演完了以后展厅里特别纯粹,我特别喜欢那种感觉,其实你在田野里头也好,在荒凉里头也好,你获得了积极劳作以后的一种寂静,那种感觉挺舒服的,我喜欢在那个空空的展厅里呆一会儿。

2016年,萧昱参展“线索·三”,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雅昌艺术网:这次个展“易位”已经是在佩斯的第四次个展了,展览是尽量不把空间填满,其实新作“竹子”的作品有很多件,但只选了八件,而是看起来像是只有一件作品。
萧昱:07年我做过一个个展,那是我的一次叙事的尝试,好处就是让我尝到一个展览老少闲宜。所以那个展览做完以后我就特别谨慎,从那儿以后我就反过来,因为搞不好就是一个庙会,一个老的观念艺术家不一定就一直在观念上有多大的突破,也许你现在做的很观念,年轻的觉得你不在系统里说话,根本不理睬你,这个很危险。有的时候观念艺术家在艺术体制里就像春天的韭菜一样,一碴儿割完了就换新的了,因为认知世界的方法、审美感官时髦的那种东西都会替换,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每次展览做完以后我实际上都有一个反思,07年到09年对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反思,后来很怕做太多展览,因为我觉得做多了对我来就变得不难了,这种状态是要警惕的。
雅昌艺术网:崔灿灿您怎么看刚才萧昱老师说的这个状态?
崔灿灿:13年我跟萧昱合作过一个个展。去年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也见到他的作品,当时展出的就是2014年在佩斯做的作品。我去看老萧展览的头一天去了伊斯坦布尔最大的一个市场叫大巴扎,里面各种东西方文明的商品,第二天再去看萧昱的作品,重新思考土地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输出等很多问题,因为所有的土地都涉及到生产、输出的问题。策展人给萧昱的位置特别好,是大展厅进门的地方,然后牛变成了驴。那个驴子就特别符合当地的感觉,涵概的信息足够丰富,不停地通过这个信息撕开一个口子,作品就是饱满的,能看到紧张关系,关于土地的紧张关系,劳动的紧张关系,边界的紧张关系等等。
我今天看任何展览有一个习惯,现实首先给你一个情绪,你不是一个空白之人进入展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萧昱的竹子在北京展的时候,中国最近发生的所有的事都会作为你的背景,具体指向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你的一种感知,这个感知就像一个移情作用一样,这个移情作用就是紧张关系无处不在,又随处可见。
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从耕地那件作品开始,在萧昱的作品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点:即第一个知识,曾经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这个知识又因为什么发生了改变,又是什么导致它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又将知识的意义和他的可能性引向了何处?
我们通俗易懂一点地讲“竹”是我们理解中的一个亚洲文明、东方文明的象征。竹子最早也是一个物品,只不过后来我们通过文人画这样一个情绪赋予它一个知识、赋予它一个结构,可是在萧昱这里,作品又回到了物质,我们没有办法就像老萧写:每天都有日出,可是我们知道最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上帝给万物命名又给万物经过社会的发展赋予了一套秩序,而这套秩序在我们适应的时候不断地依据自身的欲望也好、秩序也好重新改变它,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历史是不断被加工、质疑、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萧昱的作品中你能看到知识的变迁,我们了解一下萧昱90年代末做的作品,那种新千年即将开始,一个历史宣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在萧昱那时的作品中我能感受到一点就是物质灰飞烟灭,很多我们已有的系统灰飞烟灭。这就面临一个问题,造反派我们都能当,改革派我们都能当,颠覆派我们都能当,可是当物质灰飞烟灭之后我们如何再去定义物质,重新赋予物质一个新的生命和可能?我们不能说萧昱这个新展览给了竹子属性什么新的定义,至少他让我们看到一种临界状态,这个临时状态不是通过观念去描述的,他是通过视觉感知力,这也是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在今天这样一个系统、社会里边,艺术能提供什么呢?是一种更深刻、更富有移情作用,更容易被我们感知的一套视觉经验,这个视觉经验相对文本来说更生动,更有体温、更有血肉,更能让我们感知到那样的一个场里面每个紧张关系是怎么形成的。
萧昱这几年的展览我都来了,觉得挺有趣的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他的几个展览之间的关系是彼此连接、回应的。很多人会说“竹子”好像是萧昱经常出现的符号,现代主义谈到一个概念是我们不能重复,对后现代来说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一个同样的作品放在不同的语境里边的指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同样的一个事件三年前是一个样子,今天碰到一个别的浪潮这个事件可能会被重新撬起,它有可能成为今天一个新的事件的导火索。
萧昱这几次对竹子这个材料的使用,其实每次不是说给了它一个属性,而是重新勾连了竹子与外部的关系,这个外部的关系指的是历史的文明,指的是我们的现实,指的是我们能寻找的视觉的一个可能性。就像这次展览中的竹子第一次用铜来做,这种纪念碑式的材质跟我们对竹子的理解又是完全相异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认为竹子都要画的很清秀,你看水墨画里边的竹子要虚实,要有淡墨,要有浓墨,但是铜是一个特别直接、特别硬的,包括之前用的水泥,你还是能意识到萧昱选择材料都是挺硬的,那个意识、感官我觉得还是挺强烈的,这是我对萧昱的一个个人理解吧。

2016年佩斯北京个展“萧昱:水泥楼板”展出现场
雅昌艺术网:“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眼里的日出”是这次展览写在墙上的前言里的一句话,萧昱老师可否分享一下为什么选择这句话?
萧昱:崔灿灿刚才提到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那件作品,这个展览讨论地缘需要的知识背景更具体,这涉及到人类文明在不断地覆盖或是不断地干扰的过程当中相对开放可以很快进入思考。
说实话以前我在佩斯北京做的展览跟地缘政治没有关系,我觉得最终艺术品怎么被言说的一个现实就是“当代艺术可被不同的情况解读”的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很有趣,让艺术变得不同,就是生命力开始不同,可以讨论任何事情。我那件作品也一样,到了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展览里头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首先他们农场里帮我找了好多牛让我去挑,我发现有一只驴,因为这是我们曾经对着西域的一个想象,包括耕地的犁和中国的也不一样。虽然是一个作品的呈现,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情况下,那样一个展览、那样一个语境里把它改变了。我不太再强调它有很繁重的劳动,只是想再现人和动物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伴侣关系。
所以我在土耳其也发生了变化。就是我的作品也被我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改造,因为我觉得那样变得恰当了。如果你很敏感,你自己就会跑偏,比如我去天津超过三天,我的口音里就带着天津味,这是艺术家比较有趣的地方,也比较难。
崔灿灿:萧昱的作品这几年有一个挺大的特点,是他的这种开放性越来越强,我为什么说开放性呢?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好、写作也好,当我们寻求精确的时候就给予限制,只有不表达的时候才更接近于无限,所以我们看到星空,看到很多永恒存在,这些东西是接近于无限的,因为它是一直不断地给我们呈现了最纯粹的状态。
所以竹子给人的可能性就很多,萧昱刚才讲的开放性,挺重要的是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信息,我刚才特别仔细地留意了一下一段关于日出的描述,一段关于艺术的描述,两段文字放在一块就是一个开合关系,一个日出是我相信不仅是艺术家要日出,每个在地球上活的人都要看到日出日落;那么另外一个关于艺术的描述又是很具体的,很直接的来说一个很专业化的描述,两者之间的缝隙恰恰是一个艺术家可以从事工作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萧昱作品有意思的一点。

2017年,萧昱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艺术家参展第15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
萧昱:我再回答关于日出那个问题,为什么大家看“我的日出”呢?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怎么认识观念,怎么看待艺术?我觉得艺术走到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观念上也做了许多探索,但是我觉得艺术一直有一个语言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认为看日出这个现象是一个观念的话,从观念的角度讲,你的日出跟我看到的日出有区别吗?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你要让别人去理解你的日出很特别,而且是通过一个物理界面让你感知到的话这里头就涉及到语言,所以我一直对语言很小心,我为什么说我不敢叙事,因为叙事有叙事的语言,我还是尊重职业性,我虽然可以跨界,跨界的前提是你职业的壁垒足够强大,如果你连一个身份都没有你如何跨界?
我现在都不再称我的作品是装置,因为我怕被误解,我老是躲开那个,我怕变得很主流,我的观点想法一直是溜边的,我觉得溜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那么你让你那个视角成立的前提一定是有自己的语言,所以我一点点在做私下的工作,然后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感觉以后,不在乎到底是什么符号,是不是属于我的符号,我在找一个我表达顺手的语言。所以我后来慢慢的把竹子作品开始都叫雕塑。雕塑是需要语言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开始在制作这些竹子的时候,进入我自己的惯性和感觉,我按照我的语言习惯把它重新制造或是塑造出来。有一个问题是:我用纯粹的竹子再怎么做可以发现更多的可能性,竹子身上带有具体的信息很强大的时候我又害怕,要躲开一点,做成铜的以后就解放了我自己,我老想让自己变得自由一点,这样竹子在我眼里就是玩具,竹子铸铜以后我可以把它任意组装,我不在乎竹子长成什么样,我也不在乎中国人曾经赋予竹子怎样的情感投射。我只投射我自己,但是那个东西在那儿,别人再进入的时候,甚至变成一种共识。全世界人都对东方开始有一种想象,我把这个信息关掉,是一种暗示,这个事情不用我们再去狗尾续貂了。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是如何把这件雕塑完成的,我现在大部分在做这个工作。但我对自己整体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思考还是一个全局的系统在走。只是面对工作的时候是一板一眼的,就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你是一枪一枪的打,一个弹坑一个弹坑的跳,你没法说我就是为了正义什么,这个有点儿扯淡,其实就是你如何生存,你在面临现实工作的时候是如何正确对待你的工作,这就面临到你要建构自己的系统,这样你才好意思请别人来看你的“日出”。
艺术家有自己的语言更重要,如果你纯粹在观念上花样翻新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观念有自己的时间点,或者说有时效性诸如此类,甚至有强烈的对应关系。比如有一些艺术家更多的介入了社会生活、政治、思想,他在作品里表达观念就恰当。我是属于那个一直老想边缘,老怕被谁给算到一个堆里头,我保持一种警惕,这样也挺好的,时间长了以后我老觉得自己在旁观。私人的工作就是寻找自己的语言,但是这个路很漫长,竹子现在可能是我用的比较恰当的一个线头了,后边要织成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是肯定是在编织。不是说我只给大家看一些指导性的东西,我不是那样的艺术家。所以这个展览无关策略主题。

2017年,萧昱以“结草衔环”亮相“第六届艺术长沙”主展览
雅昌艺术网:虽然您不想被归入某一类,但是您毕竟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个艺术小组的成员,他是一个集体制的,包括政纯办刚刚在泰康空间做过一个展览。您怎么看这个关系?
萧昱:那个不是归属,那个小组一直是我特别喜欢的小组,因为人还有社会性的一面,你把自己放在那个角色里面,你的思考是不一样的,更冷静地看自己到底是谁才能知道。我09年能走出来跟小组也有关系,有一部分是我开始绝望,我老说一个无形的力量在控制着我:你被解构了,你被摧毁的时候你身上带的能量是被大家可视化的,这个能量是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社会性有的时候就像一个无形的东西,我们小组做了一个尝试,区别于其他的小组他们是有组织结构,我们小组是漫谈型的,各自有各自的立场,最后做作品跟投票差不多,谁有一个想法以后大家一起漫谈,所以经常聊了几次一个作品都出不来。就是说我们在尝试是不是有一个群体的可能性类似悬浮物,既不靠近我,也不靠近你,我们大家都对这个集体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如果这个集体把我们每个人装进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那个小组对我们来讲更多是一个实验,一种探索。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小组将来按现有艺术的规则和系统玩的多么成功,但是也很幸运,还获得一些关注,因为我们执着、执拗的这么去尝试。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是有营养的,我们成立小组以后,因为每个人很成熟,特别清晰的能看到自己作品的走向,不太容易被带着走,如果外部作为很强大的看不见的力量,作为群体共识的时候你很快会被带跑了,因为你很容易被诱惑。如果你在经常做尝试,这种尝试像你打预防针一样,预防针是小量的毒剂,让你潜藏,把他打败就知道你自己身体自带的抵抗力,所以这个小组对我来讲是对于集体主义的一种疫苗。

2018年萧昱佩斯北京个展“易位”展览现场
李佳:我觉得最好的集体是应该让每个人发现我跟集体的其他人都不一样。
萧昱: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重要。
李佳:我觉得萧昱刚才提到边缘这个词特有意思,因为我忽然想到所谓的边缘其实就是一个接触地带,他反而比中心的地方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好比我们画一个圆圈他好像就真正的能够跟外部性的东西有相遇的可能。所以我觉得萧昱说的这个边缘其实是给自己保留了很多不停地去接触某些外部的事物的可能。
萧昱的作品和他的展览说的特别少,我觉得他是勇气可嘉的。本来竹子这个材料就有太多文化的东西在那儿了,所以如果用这个东西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冒险,但确实也是能够考虑到用这个材料会引发的某些阐释的那种陈词,他没有做任何的边界,把作品往这儿一放大家就看吧,其实他自己什么都没说,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不说,所以才把那个空间留的特别的大。

2018年佩斯北京个展“易位现场” 《易位0C》铸铜 2018

2018年佩斯北京个展“易位现场” 《易位0D》铸铜 2018
萧昱: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被误读的感觉,我曾经好多年前有过关于误读的一个访谈,我发现能够被误读的作品起码是能唤起别人一些东西,所谓开放其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答案非常清晰的话,其实作品就到此为止。
崔灿灿:我觉得表述的时候你的目的可能是一个模糊性的,但是手段一定是精确性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区分,就像我们看王家卫的电影,大家觉得很恍惚,但每一个画廊又是很精确的。我们今天试图去接近一个无限,但是如果将所有的信息全部提出的话,他跟虚无主义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是在一个中间地带,没办法完全说自己凌空而起。
萧昱:我们今天很少讨论艺术本体或语言的问题。我偷偷下点儿私功夫就是因为这不是一个时髦的话题。那种讨论门槛比较高,需要你有实践经验,所以大家应该很少讨论,甚至这个话题不时髦。慢慢地无论你的作品千变万化也能感觉到这个人的味道出来了。
我现在特别越来越怕太机智,如果你50岁了,再往后工作到七、八十岁,一个老头还很机智,就觉得有点儿奇怪。就是说你活了大半辈子没有点儿真功夫也不行,所以赶紧偷偷的练点儿私功。我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可能这个不是太讨巧。



“易位0”系列细节
崔灿灿:语言问题是艺术家必须要去面对、解决的问题,但是语言转义出来的东西必须是写作者去解决的问题。
我第一次见萧昱的作品是我在南艺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图书馆有几本书,从那时开始,对我们年轻这一拨来说对老先生有一个期许,这个期许就是他的下一个展览怎么样,可是到了50岁之后如果一个老先生还做的那么聪明的话你觉得这个事就不对。50岁还不知道敬畏,就有点儿可怕。50岁之前大家都用脑袋想问题,拼体力,过了一定年龄大家就用心想问题了,这个心是特别重要的。你的日常到底是什么,你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们再也不能假定自己刺破那样一个东西,二、三十岁时候我们说过豪言壮语:要碾碎历史的车轮,参与观念的博弈,创造一个杜尚、博伊斯式的系统,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知道有一些东西确实不一定是你做的,跟你也不一定有关系。对个人来说,50岁之后如果做的特别聪明,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奥威尔写作的时候真诚问题他就解决不了,他不太真诚,东西做的不真诚,这是一个挺致命的问题。

艺术家萧昱
萧昱:全世界很多热点,包括展览、学术热点,就像一个浮点在抖动。你不能以为你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大展、学术的一个中心,你赶上下一次就成功了,因为你是在人家那个展览系统里作为一个词汇出现的,你作为一个艺术家自己是不是有自己的系统和你是不是参加了一特牛的展览,让你觉得你是成功了,我很警惕这件事情。我有时候觉得西方的美术发育的很好了以后,系统就会产生生态,各个阶层都围绕着这个东西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有一种误读,老跟不上会失落会让人沮丧。但是建构自己的认知系统的话,我是很痛苦的,我的智力应付生活还可以,最痛苦的就是做艺术。你会有一种紧张或者是敬畏,出手之后会轻一点。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罗书银整理

分享到微信,
请点击右上角。
再选择[发送朋友]
或[分享到朋友圈]